这一次的考察,使得国家教育管理部门里有了第一批真正认识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并为之说话的人。而同时,这种变化也使得徐万茂信心大增,他开始有了更大的打算,考察团回去两三个月之后,他索性把整个公司的系列产品全部搬到了北京,就在国家教委边上的一家旅馆里做了一个展厅,让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教科所和教材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都来参观。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展示虽然使得很多人都开始赞许这个公司的产品,但却并没能使徐万茂拿到进入教育体系市场的钥匙,他们开始提出更多的要求和规范,要求也更细,更为繁琐了。
这是其他人可能会绝望的第二个时点:事情看起来会越做越多?真的是做得越多越好,反而引来更多的看法?而徐万茂不这么想,在他看来,事情正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而且这一次官员们显然是真正开始以自己人的标准来要求这家企业了。他们开始从各个方面来要求这家企业做事的规范性,要求企业做到全面。虽然仍然是没有直接的成果,但希望显然已经临近了。
在国家级层面上成一件大事所要求的标准,也许要从徐万茂的第四和第五次入京中才能看得出来,这两次进京,专家们的要求更为苛刻,他们不仅要求企业要有产品使用后的反馈资料,而且要形成产品在课堂上使用的规范。也正是因此,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甚至还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了《劳技课教学参考》一书,以规范企业产品在课堂上的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徐万茂两年时间内在国家教育管理机构方面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其实是渐渐地软化了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作为一家企业在管理机关干涉下整个做事的环境。人们都为这个宁波人和他奉献于教育的诚意所打动。而此时,当时的新一届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和课程教材中心主任到任,他就是游铭钧。
教育界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来他是北京景山学校的校长,当年邓小平摸着一个小学生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就是在景山学校说的。因此我们知道,游司长从景山学校校长转而出任这个位置,必然是出于对基础教育有很深的理解的。果然不出所料,游铭钧一看到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的产品,就深为赞赏,拍板决定举行那个鉴定会。因此到1991年,国家教委的大门已经向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开启。
更有意思的是,游铭钧与华茂整个集团的关系,并没有到此结束。出于对基础教育的深度了解,他在退休之后还关心华茂的发展,并深远地影响着华茂整个公司在教育领域的作为。很显然,这是个干实事的人,因此他与干实事的华茂集团,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国家教委鉴定会召开后,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的产品还被推荐参加了当年的国家劳动劳技课程产品展览会。由此我们看到,实际上掌握着教育系统大门钥匙的国家教委,已经彻底地被徐万茂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内在的企业精神所感动,市场的大门打开了。
徐万茂身上的这种韧性,后来被人们总结成为浙商的"四千四万"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费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而对徐万茂来说,如果企业想着是为社会做事,总归能遇上知音。
"不过,为社会做事,同样要从前门进。只有从前门进,我们才能做到公司的长久生存和对华茂支持者的长期利益负责。"徐万茂说。
这不是一句空话。
国家教委的鉴定会,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权威部门的认可,与企业对于销售的整体性考虑加起来,徐万茂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自此之后,包括学校在内的多种机构都开始对他们产生了信任,做事变得十分快捷,加上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自己的效率和勤奋,企业的业务开始变得顺风顺水了。
"因为有了整体性的销售体系,创新地采用了与新华书店合作销售,又有国家教委的权威鉴定,又有源源不断的后续产品供应市场,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的产品在90年代的七八年时间里,度过了一段黄金时光。"徐万茂说。
全国化销售的力量,不仅在于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的产品有了比较好的销售业绩,更在于由于产量加大之后,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开始下降,公司就有能力把单价降下来,从而使产品竞争力全面而有效地超越对手。此时,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的产品不仅在全国各地品质都属上乘,而且价格也常常比生产同类产品的小厂要低,所以市场的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本文摘自《商学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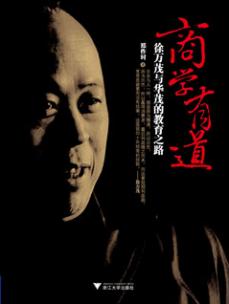 在宁波有这样一家“中国500强”,从制作竹制品起家,之后致力于开发孩子动手能力的劳技课教学具,而后多元化涉足国际贸易、房地产、化工等产业;40年来,它怀揣教育的理想,经商办学,踏踏实实地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进;如今,华茂集团已执业界之牛耳。
在宁波有这样一家“中国500强”,从制作竹制品起家,之后致力于开发孩子动手能力的劳技课教学具,而后多元化涉足国际贸易、房地产、化工等产业;40年来,它怀揣教育的理想,经商办学,踏踏实实地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进;如今,华茂集团已执业界之牛耳。在现在这个崇尚发展速度、追寻商业奇迹的社会,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好企业?回溯企业的盛衰成败,我们发现,判断企业价值的标准远非营业额、销售收入或者利润,而是这家企业是否对社会产生了长久而积极影响。
如果以上述标准衡量,华茂集团绝对是一家值得称道的企业。追逐自己的追求而不求虚浮之名,究竟是怎样的经商之道,让华茂能够40年依然树木长青?又是怎样的教育理想,让其创始人徐万茂怀着一颗代代办学的赤子之心?